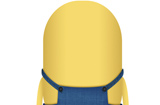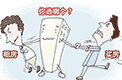“烽火連三月,家書抵萬金”——走進“搶救民間家書”組委會辦公室,翻開工作人員精心征集的一封封紙張發黃、字句發燙的抗戰家書,那一刻涌上記者心頭的感慨,便是這兩行每一個普通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詩句。回望歷史,在那外敵入侵、郵路困頓的抗戰歲月裡,一封通親情、報平安的家書對一個家庭是何其重要!家書又是不會說謊的歷史文件,這些寫於60多年前的普通家書,記載了一個個中國家庭在抗戰期間所經歷的苦難和奮爭,它們以朴素的筆觸,勾勒出親情背后的大時代,重現了其他載體無法傳達的歷史場景。今年是抗戰勝利60周年,半月談雜志首次發表這些出自普通中國人之手的抗戰家書,以期使人們從中反思戰爭的罪惡,領悟和平的可貴,理性看待友好睦鄰背景下的現代中日關系,攜手開創更美好的未來。
“亂世做人,簡直不是人”:一個小學教員的悲憤呼喊
“我對他了解很少”,今年71歲的上海老人姚慰瑾在電話中對記者這樣談起她的父親。在她4歲那年的1938年,父親離開已經淪陷於日寇之手的上海到外地謀生,僅僅半年后便杳無音訊,據說因貧病交加而死,但無從知道死於何處。她已記不清父親的模樣,也隻能在長輩的敘述中大略勾勒出他的形象:他叫姚稚魯,是一個普通的小學教員,為人耿直,疾惡如仇,對親人和朋友具有愛心,非常愛國,詩、書、畫都很好,常常給人書寫扇面、寫“百壽字”做壽禮,等等。除了一兩張模糊的照片,父親留下的便是一些抗戰期間離滬后寫給家裡的書信。今年4月,當國家博物館等單位啟動“搶救民間家書”項目時,姚慰瑾決定把這些信捐獻出來,她說:“這些信也許態度有些消極,但卻反映了戰爭給一個人、一個家庭帶來了多麼大的災難。”
事實上,這些信不僅記錄了姚稚魯——一個小學教員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后蹤跡,也為抗戰期間的民間景象留下了鮮活的第一手記錄。1937年8月,淞滬會戰爆發,姚稚魯一家所在的上海南市區老城廂很快陷於敵手,百姓紛紛逃難,姚稚魯率妻子馬芳珍和兩個女兒慰瑾、亞瑾逃往法租界妻兄家。1938年4月,性格倔強的姚稚魯不願依賴親戚過活,不顧有病在身,決意孤身一人離滬去外地求職。
離滬后,姚稚魯先后到過南昌、武漢等地求職,均無結果,1938年8月便徹底和家人失去了聯系。由於這一階段先后爆發徐州會戰、武漢會戰,當時的國民政府集中兵力和日軍展開決戰,華中一帶兵荒馬亂,難民如蟻,貧病交加的姚稚魯最終死於戰亂之中是極有可能的。他先后寄回上海的信也能看得出寫於匆忙之中,紙張大小不一,日記、書信形式各異,落筆草草,倉皇之勢顯然。他離家不久在南昌寫的一篇日記裡提到“霎時誤傳警報,群眾紛避,我方驚愕間,乃稱並無其事,可笑也。余之生死,早置度外,飛機炸彈等閑視之。故余所至,如溫州亦曾被襲,麗水於前數日間飛機光顧至二三十架之多”。
在南昌期間,他沒有找到職業,心情極其郁悶,又接到家裡來信說小女兒亞瑾出痧子,心如刀絞,在回信中寫到“‘死’是人所怕的,到了死,甚麼都丟了倒也干脆,像我活又活不了,死又死不了,這罪真夠受哩!”由於戰亂,南昌當時缺醫少藥,姚稚魯灰心地寫到“看一次,起碼得四塊錢,叫我出得起嗎?……我的病,生在破家失業的時候,就是該死!我想要是早兩年生這毛病,怕不至於到此地步吧!”
姚稚魯在南昌一信的最后,提到他所目睹的難民生活,借此寬慰妻子:“話又說回來了,天降劫數,遭遇不幸的,不是我一個,就像我們那裡住著一家姓鐘的,他們在泗涇有田地有房產,他自己在上海當教員。開戰之后,他一家子帶了千把錢逃難,一路出來,東西也丟了,錢也用得差不多了,他夫婦兩個帶上三個孩子,還有一位老丈母,住在示和裡,看他們一家六口,每天限定吃一粥一飯,小菜嗎?不過化幾分錢,真節儉極啦!……還有一位是在蚌埠開洋貨店的老板娘娘,逃難的時候和她的丈夫失散了,抱了一個小孩子,不過五六歲的罷,在點心店裡求乞,我想像這種情形的一定不少,那麼你比了他們好了!”
之后,姚稚魯又到了武漢投靠親戚,但武漢已經處於大會戰前夕,人心惶惶,他仍舊找不到合適的職業,下面這封信,便是他留下的最后幾篇書信之一,其中的絕望和悲憤情緒無疑是對戰爭的最大控訴:
離開上海兩個月了,在這裡隻有憂愁苦悶,白白的吃了人家的飯,魚啦肉啦,誰虧待了我呢?不過總是一個不自在,失業的痛苦,真夠味哪!
在中原大會戰的准備聲中,武漢密布著恐怖空氣,走啦!走啦!重慶、成都、香港、上海,紛紛地忙著奔波,我呢,滿望到了漢口,或許在生活上有一點兒希望,如今可毀啦!不單舍卻你們,在外面度那可憐歲月,而且要跟上四姊逃難哩!……
在武昌碰見了孟志杰、畢映泉,說到了上海的家中,隻有付之一嘆。盧炳章也到了廣州,據說生意很不差,不過前幾天廣州遇到大轟炸,不知道怎樣了?亂世做人,簡直不是人,過到哪裡就算,也憂急不了許多。這幾天,這裡謠言很大,說要“轟炸武漢”,管他呢!“在劫不在數,在數最難逃”,我便聽天由命吧!
寄上的小照是四姊去年在南京照的,她是走運的一個,可是現在腆著一個大肚子,要在輪船大車上擁擠,也很可憐的了。
……
“讀書仍為重要”:生生不息的民族傳統
抗戰期間,無論是在淪陷區、戰區,還是在大后方,每一個中國家庭都籠罩在戰爭的陰雲之下,正常的生活秩序已經被完全打亂,國家、民族和個人的命運都不可知。但是,許多身為父母的中國人仍念念不忘對子女的教育,在書信中諄諄教導,惟恐其荒廢學業,墮入下流。這種對中國特有的讀書傳統的堅持,實際上蘊涵著對未來的希望,對抗戰勝利的信心,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正在於此。
在湖北黃石市離休干部周鴻特的記憶中,就有一封這樣的信,鼓舞了他一生:他的母親湯錚訓是一位教育戰線的早期革命者,20世紀20年代曾在湖南配合黨開展婦女工作,1927年加入共青團,30年代又投入到抗日救亡和教育工作中。1938年秋,湯錚訓攜周鴻特的兩個弟弟離開湖北的家,到湖南衡陽暫住,不料由於戰亂再無相見之日。1942年,周鴻特已經8歲,遠在湖南的母親湯錚訓非常挂念他的學習情況,寫來一封信: 鴻特兒覽:
一別四年,無時不在念中。兒已漸長,應入校念書,今以世亂,母子離別,隻令人興嘆而已。
但讀書仍為重要,此時雖無學校可入,兒得與祖父及姑姑朝夕相依,正可習字讀書求教於長者也。
上述讀書一事,望兒努力勿怠,以慰親心。
母錚訓書
1945年,抗戰勝利前夕,身染重病的湯錚訓因輾轉流離、得不到及時治療而飲恨辭世,這封信便成了她給兒子周鴻特留下的惟一墨跡。此后,周鴻特一直珍藏著這封信,甚至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也不忘帶在身上。他兄弟四人后來都成為工程師、教授等人才,子女也都學有所成。周鴻特說,抗戰年代留下的這封信,時時激勵我和后輩們,刻苦學習努力成材,把一切都獻給我們可愛的祖國。
無獨有偶,山西省太原市的離休干部李耀東也珍藏著這樣一封抗戰家書:1940年6月,在陝西參加抗日活動的李耀東收到一封父親以雙親名義寫的信,信是從山西汾陽的老家經河南輾轉寄到陝西的。盡管戰爭曠日持久,生計艱難,這位清光緒28年畢業於山西大學堂的中學教師仍對兒子寄予了很高的希望:
耀東:於陰歷五月一十日接到四月廿七日所發之信,得知一切平善,慰甚!對於我所指各點,既能躬行實踐,即是上達之兆,你年紀尚幼,離我太早,深恐身不能修,走入墮落一途,勉之!經商之余,宜多多學字,取其收斂神氣,鎮定心思也。青年尤以養廉為第一著,但養廉必須儉,所以無論收入多寡,萬不可浪費分文,致失養廉之基,一失足成千古恨,不可不慎之於始也。
生活日艱,到處皆然,汾陽自三月以來,九十天點雨未落,二麥歉收,大秋未種,小米每石竟漲至三十五六元上下,十室九空,誠可慮也!你能和你四大叔就近團聚,實為幸事,彼此互助,獲益不少。我亦有意到你們那裡團聚一回,但道途梗阻,未知能否如願,此年老人之心情也。你姑丈既在就近,可常常請教,自有益處。……父母合示
陰歷五月廿二日
信發出的第二年,即1941年,這位老父親就病故了。然而這樣一封飽藏著嚴父之愛的信,卻讓李耀東珍藏了一生,也鼓舞、鞭策了他一生。
“為了保護我們的家庭”:兩個戰士的心聲
在陰雲密布的抗戰歲月裡,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、新四軍是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。這裡有兩封來自抗日戰士的信,便一掃戰爭的陰霾,充滿了革命者對勝利充滿信心的豪情和樂於奉獻自我的情懷。他們在家書中不但對親人表示了由衷的關心,也通過自己的書寫讓親人受到勝利的鼓舞。也許,這便是我們能夠持續八年抗戰、最終迎來勝利的力量之源吧!
有一封紙張發黃、信封破損的抗戰家書,據它的擁有者、浙江的民間收藏愛好者周立峰多方考証,它的作者是一個江西籍的紅軍戰士,經長征后到達陝北。而信寫於1937年4月30日,抗戰還沒有全面爆發,紅軍尚未改編為八路軍,但西安事變已經發生,第二次國共合作已經達成,因此信中提到了“國共合作”。這封普通紅軍戰士寫給江西老家的信流落民間,被周立峰在一次拍賣會上取得,其作者下落已不可考。從行文上看,作者文化水平不甚高,文法上有多處不通順的地方(括號內注釋為記者所加),但談到抗日的情況時卻流利而鏗鏘: 父母親大人膝下:
敬稟堂前萬福金安!進(近)來身體是健康,飲食增加不?……(此處筆跡不清)想必家中合家平安,同家安樂,但是我離家已(以)后已有(許)久了,自從反攻以來未曾與家通信,我想家中就(像)是忘了我一樣。自我反攻以(已)到達陝西栒邑縣太峪鎮駐房(防),衣食住行是很平安,請你在家不要挂念。
但是自三原與家通信一次,也未曾(知)家內接到了(沒有)?現在也未見回音來,可不知家內怎麼樣?自我現在的國家,不過說在外便為了國家的事情。我在外,大家都是為著抗日的,為了保護我們的家庭,為著自己的來做事!不過現在說起到達北方,使用國共合作、釋放一切政治犯,聯合許多了(的)抗日友軍,國家已經和平。但是我家(有)沒有什麼問題?假是(使)家內接到我信,很快的與(於)家來信,不要遲慢,免得我在外挂念。來信到第一方(面)軍第一軍第四師十二團第三連。工作是很快樂的!
金安!
兒 鐘士燈啟 陽歷四月卅日
與紅軍戰士鐘士燈於軍旅生活中匆匆揮就的朴素文筆相比,新四軍戰士胡孟晉離開故鄉時給妻子寫的信就顯得格外生動活潑、深思熟慮。胡孟晉,安徽舒城人,自幼勤學,成績優異,20世紀30年代從師范學校畢業后一直在家鄉推行白話文教育,抗戰爆發后參加了新四軍戰地服務團,從此投身抗戰,轉戰於安徽、江蘇之間,后又隨新四軍北撤,1947年在山東逝世。這封信寫於1939年,當時胡孟晉從前線回鄉和妻子張惠團聚,臨別時給妻子留下了這封精心撰寫、語重心長的信,信中對妻子作為革命伴侶的思想進步寄予了很大的期望,當然也不乏夫妻間熾熱的愛,這從該信抬頭上點綴的“戀”字就可見一斑: 最親愛的惠呵:
我們又要離別了!當你聽了離別的聲音,或者不高興吧!
親愛的,誰不願骨肉的團聚,誰不留念家庭的甜蜜,要知道國家民族重要,個人前途重要,因此又要別離親人,而遠赴他鄉了。
為了你的寂寞,為了你的思念,千裡外的我,暫時停了救國的工作,越津浦跨淮南,到達別離一載的故鄉來。二月來的團聚歡談,暢言國事,解釋問題,你的政治水准提高了,民族意識加強了,革命的陣營中,增加一位健將了。
畸形發展的中國,教育不普及,人民的知識簡單,而婦女尤甚,隻要家而不顧國。大難當頭,應踴躍赴前線殺敵,而婦女們阻礙其夫或其子之偉志。希望你將無知識的婦女組織起來,宣傳和教育她們,使伊等知道“皮之不存,毛何附焉”?“國之不存家何在”?使她們不致含淚終日,倚門遙望前線上的夫、子早日歸來呢!(望勝利歸來)
惠,最親愛的人,你是婦女中先進者,對於我這次的外出,請不要依戀,要知道你愛人的走,不是故意的拋棄你,而是為著革命,為著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努力奮斗的啊!
家庭經濟之困難,生活之痛苦,我是深知的。要革命成功,須經過困難艱苦的階段,當此環境中是要立定腳跟,具堅強之意志,任何之外誘不可動搖的,“國危見忠臣”,在困難中鍛煉成真正的革命者啊!
富貴反多憂,錢是要人用,不要給錢用了人,在此抗戰時,多少富翁成寒士,由此看來金錢不足恃也。對於窮人要客氣,要同情他。對富人也要與對普通人一樣,對於守財奴,少與之來往,因為他隻認錢,不認人,這些人不要看起他,但與之面子往來而已。
惠呵,我們要認清時代,當此革命時期,家庭衣食可維持就夠了,不要有其他念頭,要知道整千整萬的難民,千百萬的勞苦大眾,生活是多麼的痛苦呵!人生是要做偉大事業,而不是做了金錢的奴隸呵!太看金錢重的人是最污臟的,不要與之往來。
愛人呵,你在無事的時候,多多閱讀書報,可使你知識進步,多多想工作的方法,切不要空想,也不要太挂念在外的我,勞神傷身,於事無益。好好教養二個小孩,切忌打罵。處家事,對外人,言語態度等等,可參考我的日記和通信,要切實的做,不然我的心思枉費了。請你真正的做吧。否則,太對不起在外的人呢!
最親愛的人,你不要太念我,你的厚情,我是知道的,我不是個薄情的人,請你放心,決不辜負你的熱情呵!
在外的我,身體自知珍重,一切當知留心,請你安心在鄉努力婦女解放的事業,成為女英雄,我在外對革命之偉業必更加努力呵!別了,別了!
此致敬禮
廿八、十一、廿八,群於舒百
而這位張惠女士果然沒有辜負丈夫的期待。據這封信的捐贈者———胡孟晉烈士的生前戰友、82歲的離休干部張軾同志向記者介紹,張惠隨后便在家鄉投身於“婦女抗敵協會”的組織工作,在胡孟晉烈士逝世后又撫養幾個孩子長大成材,至今仍以91歲的高齡健在。

 分享到人人
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
分享到QQ空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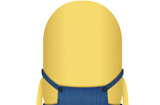

 恭喜你,發表成功!
恭喜你,發表成功!

 !
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