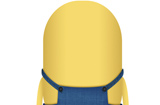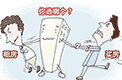據史料記載:北宋時期博州有位州官,為官極廉潔。一天晚上,他收到一封上司的來信。他猜想一定是朝廷有什麼要事,馬上令公差點蠟燭閱讀,讀了一半他又讓公差把官家的蠟燭吹滅,把自家的蠟燭點上,繼續往下看。公差們對此很納悶,難道官家買的蠟燭不及他自己出錢買的亮嗎?后來才知道,那封信裡有一小半是關於他留在京城的家屬的情況的,他認為這是私事,不能點官家的蠟燭。
為了半封家書竟然換燭再讀,這在許多人看來頗有幾分“迂腐”,別說是用官燭看半封信,就是一封信、十封信、百封信,也不會有人去“斤斤計較”。因為用根蠟燭是再小不過的小事。可是就這麼一件小事,這位州官卻看得很重。可見他的頭腦中,“公”與“私”的界限是多麼分明。
這就是儒家思想教育的典范。
再看看我們的現實生活中,一些人“公”與“私”的觀念卻遠不如那州官分明。明明是單位工作用的電話,卻有人用它打私人長途,且一打就是幾十分鐘﹔明明是公車,卻經常用它辦私事﹔明明是集體的財物,卻想方設法讓它們長上“翅膀”,飛到自己家裡。更有甚者,有人干脆把“公”與“私”作了顛倒。
喜歡佔公家小便宜的思想要不得,更放縱不得。俗諺說:“金錢如糞土,氣節勝黃金。”清朝張伯行曾言:“一絲一粒,我之名節﹔一厘一毫,民之脂膏。寬一分,民受賜不止一分﹔取一文,我為人不值一文。”一方面,貪佔公家小便宜,使人失去了氣節和人格,得不償失﹔另一方面,它會促使一些人滑向墮落的深淵。俗話說,有了第一次,就有第二次﹔小時偷針,長大偷金。許多人之所以腐化墮落,就是由於有了“第一次”和不能慎微,而一步步滑下去的。
在處理“公”與“私”問題上,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准確把握自己,像滅官燭看家書的那位州官一樣,認真對待生活中的每件小事,做到公私分明,不貪不佔。

 分享到人人
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
分享到QQ空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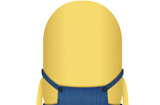

 恭喜你,發表成功!
恭喜你,發表成功!

 !
!